
- P-ISSN 3022-0335
- E-ISSN 3058-2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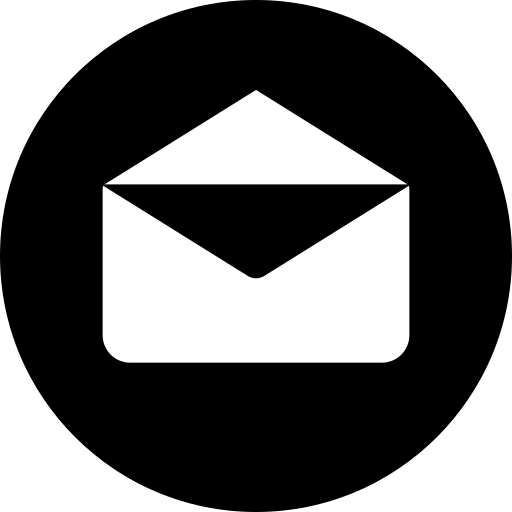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Guo Xiang's Commentary on Zhuangzi has four meanings. One is freedom as understood via ontology, which presupposes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 freedom as the absolute freedom of the "Dao" of all things. This freedom is fundamental but abstract. The second meaning is freedom centered around the individual. Individuals cannot directly perceive the "Dao" ontologically and can only experience the determined side of it as a "transformed" object, and their freedom is limited. The third is the freedom that is centered upon the "Dao." The freedom that individuals truly experience through practice is the absolute freedom of dissolv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ontology. The fourth is the freedom of subjective choice. One's degree of individual freedom depends on their subjective freedom of choice. Through Zhi Daolin's new interpretation of freedom, it can be seen that Guo Xiang's view of freedom has limitations such as defending an unreasonable ruling order and lacking practicality.
硕博士均就读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佛教的缘起论和无生思想以及中国禅宗。研究成果有在第七届佛教义学论坛发表论文《"易行道"思想变化研究------从〈十住毗婆沙论〉到昙鸾、道绰和善导》;于《西部学刊》发表论文《成玄英〈庄子疏〉中的生死观》等。
郭象(约252年-312年)的自由观体现在其本体论、"性分""独化""相因""玄冥之境"等学说中。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自由因本体或现象、可经验或被遮蔽、只能顺应或可以选择等差异而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维度,在不同的自由维度中,个体对于自身命运的决定程度和参与程度也是不同的。
郭象的本体论顺应了魏晋玄学本体论转向的风气,以境界性的阐释作为解释万物本源和本体的重点,同时超越了"崇有论"和"贵无论",避免了有无两极性解释的误区,也就成功阐发了一种不被"有"或"无"等任何对待所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本体,为其自由观提供了根本依据。
在郭象把万物的本源和本体论述为:"初,谓性命之本。"(Guo 2013,第492页)"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Guo 2013, 383)。
在郭象看来,万物的本源"有之初"和万物的本质"性命之本"是一回事,都表述为"初"或"一",如果继续向"初"或"一"之上追溯,那么"一之所起,起于至一",这个"至一"不是"无",不是物理性的存在,故而也当然不是"有"。所以,在郭象看来,万物的本源和本质是一种非有非无、无相无形、无资无待的存在。这种存在,也被称为"道""天"或"自然":"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Guo 2013, 69)。"道不逃物"(Guo 2013, 662)。"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Guo 2013, 56)"天者,自然也"(Guo 2013, 423)。
可知这些本体论的概念,既是对万物本源、也是对万物本质的描述,从郭象对这些概念的论述中,可以对万物之自由性进行分析:
"初"偏向于对本体的时间性阐释。郭象既然将"初"解释为"性命之本",可知此处的时间性并不是指本体先于物,而是指从有物开始"有之初"本体就不离于物。"初"不依靠什么不可捉摸的"无"或有为造作的"知",同时"初"又与"无"等同"屡称无于初",可知万物依靠内在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而自生"自得此生",而且一旦产生,就具备了"无"这无任何规定性的绝对自由的本质。
"一"和"道"偏向于对本体的统一性阐释。万物皆"自得""自生",这是"道"的特性所现,看似是"道"所规定的,但"道"这种规定性又是无规定的,因为万物"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这样,"道"作为万物的本体,不处于是主宰非主宰、有规定无规定的任何一个极端,这就保证了"道"的绝对自由,也确保了以"道"为本的万物在本体层面的绝对自由。
"天"从中国哲学整体语境上来看,偏向于对主体的主宰性解释,但在郭象这里,"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適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Guo 2013, 51),可知万物并没有一个实在性的产生者和主宰者。郭象把"天"解释为"万物之总名",如果理解为"万物统称为'天'",似乎不合常理。结合郭象对"天"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天者,自然也""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天"可以理解为万物皆有之本体。可知在郭象看来,"天"作为一个极具权威性的存在恰恰代表了万物自由的权威和绝对性。
郭象把"天"和"自然"等同,"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Guo 2013, 51),"天"使之然就是"自"使之然,也是万物的本性使然;"自然"既可以是名词,作为对境界性本体的描述,又可以是动词,即万物瞬息万变的"这""然"正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如此着。所以,本体的自由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一种没有指向性的单纯的"力",是源源不断的从万物自身流淌出的自由无为之力。这里可以看出郭象对老子之"周行而不殆"的"道"的本性的继承和发展,即,"道"以"力"的方式存在,作为万物的原动力,"道"就是"力"本身,其力的运行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是自由所发的,作为动力的自由使自由不会仅仅局限于本体,而是贯穿于本体显化为现象、现象的生灭变化、现象复归于本体等一切过程中。
通过上述本体性的概念可以得知,万物皆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万物内在固有的本性"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和动力,是从有物之初就存在的天赋之权。作为本体,这种自由一方面在郭象看来是真实不虚的,可以作为现象界的自由的根据以及超越现象界的自由的动力;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在没有被经验到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预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郭象所处的魏晋时期,普通民众是局限于现象界的,本体的难以经验导致了本体性自由对于"凡人"而言无异于空中楼阁。所以如何将自由落实到现象界是郭象需要重点讨论之处,为此他提出了"性分"的观点。
何为"性",郭象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Guo 2013, 475)。 "以性言之,则性之本也"(Guo 2013, 219)。"自然耳,故曰性"(Guo 2013, 614)。可见,不同于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主要从万物普遍具有的共同的本性的角度谈"性",郭象虽然也认同"性"是自然的、本质的,是万物变化的依据,但他侧重于"性"的个体特殊性(Pan 2013, 8)。这种具有个体差异的"性"是有一定的分量、极限或程度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Guo 2013, 120)。"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Guo 2013, 78-79)。
可以推断的是,"性分"并不在本体界,而只存在和运行于现象界。因为"性分"包含了界限、分际之义,而如上文所说,万物的本体是"一""天""道""自然",这些存在是没有界限可言,所以"性分"只能作为整体性的本体在现象界的显现。虽然郭象给"性分"赋予了本质性的含义"以性言之,则性之本也",但这个层面的本质并不具有终极性和本源性,只是现象界事物背后的规律,好比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背后的规律是地球的自转运动,而这种现象和规律的最终根源和本体在郭象看来是具有推动力的"道"。
通过"性分"所规定和达到的自由是个体本位的。这种自由是从个体内部、个体自身的角度而言,个体在其"性分"之内是圆满的、自由的,具体表现为三重含义(Xu 2011, 16-20):
其一,个体产生于现象界之初所具备的自由的程度由"性分"所限定"物各有性""性各有极",它表现为个体生来具备的生理、精神状态和能力,这限定了个体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自由的程度。如"夫曾史性长于仁耳,而性不长者横复慕之,慕之而仁,仁已伪矣"(Guo 2013, 28),曾子之所以在后天可以达到如此高的道德修养,是因为他先天具备了优于常人的"仁"的能力。
其二,个体后天社会性的自由被"性分"所规定,即个体后天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的限度、范围、规范等。个体生来具备的自由和社会性的自由被郭象区别为"性分之内"与"性分之表",每个个体保持自己的"性分"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即是其他个体自由实现的基础,反之则会造成天下大乱:"安用立所不逮于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驰而不能自反哉!"(Guo 2013, 326)
其三,这种有限的自由的现实是通过"适性"的方式成就"性分"。"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Guo 2013, 1)。每个个体只要在其"性分"中安分守己,充分实现其"性分"中本有的能力,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就是自由:"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Guo 2013, 10)。
由于每个个体都具备并趋向于实现自己的"性分",所以成就了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相因"状态:"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Guo 2013, 513-514)。 "相因"在郭象看来,指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需要借助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即有一定的条件性:"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Guo 2013, 65)。"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Guo 2013, 513)万物在彼此相与、相济的同时,必然相互制约,因此"相因"在个体本位层面既是个体自由实现的条件,也是个体自由的限制。
由于个体生来所具备的"性分"是自然的,"相因"也并非刻意为之,这就是"独化"。郭象认为,"独化"是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没有任何原因和依待:"独生而无所资借"(Guo 2013, 654)。因为如果推寻事物产生的原因,最终只会推至"没有原因"的"无极":"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Guo 2013, 105)所以,万物无论是产生还是生后的存在过程都是"自"使之然,如前文所说,即是本体、本性使然:"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Guo 2013, 348)"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Guo 2013, 51)因为是自己的本性使然,所以是"自因":"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Guo 2013, 71)。
"独化"和"相因"看似有矛盾,其实不然。因为"相因"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正是"独化""自然"的体现:"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Guo 2013, 220)。"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与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识其所以哉!"(Guo 2013, 106)
但在个体本位层面,"性分"虽然本质上是个体本有之"天""道"经由"独化"自然而生,从本体层面而言,个体自身便是其"性分"的决定者,但是当个体尚未经验到本体的"天""道"的时候,虽然同时作为"独化"的主导者和所"化"的对象,对于个体的主观体验而言,由于无法体验到作为"独化"的主导者的"道"的一面,所以无论是对于"性分"所表现的必然性的"命"还是偶然性的"遇"或"时"(Luo, Cai 2021, 123-130),个体只能感受到被决定的一面。"自"使之然、"自因"这一决定者的一面因无法被经验到而被遮蔽,故以"他因"的形式表现于个体的经验中。而且,"道"为什么会形成个体这样的"性分"而不是其它的样子,个体也无从得知,只能诉诸"道"的无不可的自由性。
可见,对于个体本位的自由,个体除了守分安命以外无能为力。因为个体在自己的"性分"之外会处处碰壁,个体囿于现象界的时候,自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行使,没有可能从外部获得,因此可以说,自由诉诸个体本位是不乏无奈和辛酸之举。
不同于本体层面抽象预设的自由,在郭象看来,"玄冥之境"是可以通过一些道家的实践方法真实体验到的自由之境。
如前文所说,本体作为一种非有非无、非有规定非无规定的存在从来都与现象同在,这决定了万物绝对自由的本性一开始就与万物共存。个体的本性即是无限的、绝对自由的"道","道"无规定的规定了个体"性分"的个性作为个体在现象界的显现方式,同时,"道"也无时不作为个体在本体界的存在方式。所以个体从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同时是整体性的"道",因为"道不可隐""道不逃物","道"是没有规定性的,所以它非个体非整体,也即个体即整体。个体从现象界的角度看来,处处是被决定的、有限自由的,而从本体界的角度看来,是决定者、绝对自由的,如果说个体本位的自由观摆脱不了一种无奈的意味,那么整体本位,或者称之为"道"本位的自由观的立论情绪则积极得多。
这种"道"本位的自由与"性分"说及其认证的个体本位自由并不违背,只是因个体所处的境界不同,所以享受的自由层次和程度不同而已。"道"本位的自由所处的境界是超越了现象界而达到现象与本体泯然一体的"玄冥之境"。
郭象认为"玄冥之境"是个体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Guo 2013, 234),在此境界中,个体"彼我玄同""与物冥合"。在"性分"的观点中,每个个体在现象界因自己的独特性而与其他个体相区别,个体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要想跨越只能是个体印证入本体界,达到现象与本体的通融无碍,通过万物皆具有的统一性的本体实现自身与他者之间的无障碍"连通",而且这种玄妙的连通不是抽象的和理论上的,而是可以被个体所主观经验到的。因此可以推断,"玄冥之境"是个体与自身本有的本体"道"印证为一,个体可以超越现象界肉体等限制,无障碍的直观本体,此时现象与本体的分界已经被消解,或者说,只保留了形式上的区分。现象界的"性分"由本体产生,或者说,是本体的显现,如郭象言:"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Guo 2013, 561)。1当个体局限在现象界的时候不得不受"性分"的约束,享受有限的自由,但本体界并没有分际可言,处于"玄冥之境"的个体"玄同万物而与化为体,故其为天下之所宗也"(Guo 2013, 225)"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Guo 2013, 65)"物有際,故每相与不能冥然,真所谓際者也"(Guo 2013, 664)"不際者,虽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際其安在乎!"(Guo 2013, 664)在本体的"道"的境界,处于齐生死、齐万物、齐物我的状态,没有物之间的分别,故万物之间的分际和障碍就形同虚设,此时,个体不受任何限制,在保持自己现象界的独特性不丧失的情况下同时拥有本体界整体性的"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绝对的。
在"玄冥之境",个体可以同时经验自身作为"独化"的主导者和所"化"的对象,此时,"独化"才真正成为与个体直接相关的事,因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个体才实现了对"独化"的直观,真正成为了"独化"的主宰者,成了"造化"本身,而不仅仅作为所"化"的对象参与其中,如郭象言:"冥然与造化为一,则无往而非我矣"(Guo 2013, 120)。"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Guo 2013, 105)。"独化"所强调的是万物产生和变化的自由性和自主性,郭象否定一个有为的造物主的存在,其目的便是将产生和变化的主动权还归万物自身,但如果个体连经验都经验不到,那还有什么主动可言呢?所以唯有在个体冥合于"道"的"道"本位层面,"独化"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和确证。
个体"独化"的真正实现,并非不再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条件,如郭象言:"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Guo 2013, 220)"独化"并非指个体独自产生和变化,而是强调个体产生和变化没有有为的主宰者,完全是个体自身的"道"的自然运作。由于"道"的普遍性,为一切个体所有,所以"独化"表现为万物自然的大化流行,互为条件,个体的产生和变化是一定条件的自然聚合所导致的自然的结果,所以"独化"表现为万物自然的大化流行,互为条件,个体的产生和变化是一定条件的自然聚合所导致的自然的结果,所以"独化而相因",这二者并不是在同一等级,"相因"助成"独化"的实现,"独化"才是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在"玄冥之境"中,"相因"作为个体实现的条件,不再成为个体自由的限制。因为"相因"的自然性和自由性,只有在"玄同必我"的境界中才能被直观经验,而在现象界的彼我分际的思维中,事物之间的对待关系是绝对的、僵化的,因此彼此的制约关系也被固定了下来,陷入了"他因"的虚妄模式中。只有冥合于"道",对"独化"的"自因"有直接的体验,事物之间的对待关系才能被纳入自然、自由之中。
上述自由的三重涵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体自身具备的整体性的"道"的运作,其区别只在于"道"的运作作为基础还是表现、现象的还是本体的、被个体经验的还是遮蔽的,既然是"道"的无为之作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的,就算是个体能够经验到并作为"道"之本体参与其中,似乎都与个体的主观选择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一切都是"道"在"为",与个体的后天意识的选择无关。这似乎与宿命论区别不大了,二者的差别无非是,在宿命论的观点中,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事无巨细的决定着个体和社会发展的一切,而在郭象的学说中,那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个体达到"玄冥之境"的时候变得可知。郭象并不是宿命论者。尽管他在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主观意识的选择,但这一层自由从他的学说中不难推断出来。
首先,从"性分"学说来看。郭象认为"性分"是"道"无为而自然的"独化"而产生的,是必然而不可更改的,但他同时也说,"然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故乃释此无为之至易而行彼有为之至难,弃夫自举之至轻而取夫载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Guo 2013, 170),世人多不能做到任性安命,所以造成了个体不能全其生、社会"奔驰而不能自反"的乱象。既然"性分"具有必然性,那为什么还能被违背呢?
其次,从郭象的"变化"观来看。郭象认为事物的"独化"都是自身"道"的自然而为,既然如此,个体对于发生在自身和周围的变化应该是无能为力而只能顺应的,但他同时也说,"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Guo 2013, 440)"居变化之涂,日新而无方"(Guo 2013, 270)。既然郭象劝导世人应时而变、与日俱新,就说明个体也可以选择违背时势。
复次,从"玄冥之境"的观点来看。道家学者注意到了世人不自由的处境,所以历来都提出了诸多修身养性的方法使其获得自由,郭象也不例外,指出"玄冥之境"这种自由的境界并提出或继承发展了"无心""坐忘"等方法,也是对世人不自由处境的医治。这说明,自由是可以通过主动追求得来的,个体可以通过选择某些修习的方法来获得自由。
以上可以推断,个体并不必然处在某种境地,而是可以通过主观意识的选择摆脱令自己不适的境地而获得自由。所以主观选择的自由是蕴含在郭象的学说之中的。上文所说的三重自由都是"形而上"的,只有可顺应性而没有可实践性, 而主观选择的自由则是落实在个体日常生活中、贯穿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实实在在的"形而下"的可实践性的自由。
这种自由与必然的"性分"并无矛盾。无论是"性分"还是内含于"性分"中的变化之时势,都是对一种可能性区间的描述,好比个体自身之"道"为个体预设的道路,个体可以在这条道路之内自由行走,也就是尝试这个区间内的各种可能,这即是个体本位的自由,个体只要不偏离这条道路,就是适性安命,如果偏离了"性分"的可能性区间,就会伤性损命,遭遇祸患,但是否行走于"性分"的道路中,是个体主观选择的自由。如郭象在注《养生主》中右师介的遭遇时,说:"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两存其足,则是知之所无奈何。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岂直偏刖而已哉!"(Guo 2013, 117)右师失去一足,是无可奈何的必然性所致,但是否选择安于这种必然性,则是右师的自由。
个体是否追求"玄冥之境"的境界,使自身超越现象界的束缚而达到现象与本体的融通合一,证入物我冥合的绝对自由领域,也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这也是郭象自由观的可贵之处,即,他清醒的意识到个体在现象界的不自由处境,鲜明的揭示个体在现象界所拥有的"性分"之内的有限自由并指出违背"性分"的后果,指出个体所能达到的玄同万物的绝对自由的"玄冥之境"并告知证达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为世人展示出了从不自由到绝对自由的所有可能性,而最终决定自己处在哪种程度的自由的是个体自身。这就意谓着,最终决定个体自身命运的是个体主观的选择,主观能动性其实从未被"性分""命""时"等必然性或偶然性遮蔽。个体选择的自由是自由最完美的体现。
支道林(约314年-366年)对于郭象自由观的批评集中于"个体本位"的自由方面,即批判在"性分"之内的有待的自由。
与庄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疏离不同,郭象明确以"经国体致"为建立学说的目的,努力将名教的体系容纳进无为之治中,所以反对将神人与圣王、隐士生活与政治生活分裂,而是用"性分"同时赋予各种生活方式以合理化,如百姓满足于当下是安于自己的"性分",圣王治理群生也是顺应自己的"性分"而为。但对这种"性分"之内的有待的逍遥,支道林提出了反对看法:"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Yu 2007, 260)可见,支道林赞同无待的逍遥,而对于有待的逍遥,他认为只有在所待"至足"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现实情况是,人很难满足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一个生命的满足有时以另一个生命的牺牲为前提,如支道林说:"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Shi 1992, 160)。这是否为君主的暴政提供了合理性?且对于受害者而言,莫非无辜的牺牲就符合其"性分"?
郭象作为"名教即自然"的宣扬者,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Guo 2013, 58),这种用道家理论维护统治秩序的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与庄子的穷困潦倒、远离政治与世俗的生活境遇不同,郭象"任职当权,熏灼内外"(Fang 1974, 1397),从其生活环境可猜测,郭象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关怀与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其依托于"性分"的"个体本位"的自由更适合于衣食丰裕的统治阶级,其通过"坐忘"来实现的"道"本位的自由更适合于生活清闲的贵族,而对于身处乱世的劳苦百姓而言,大多只能用"安于性分"在战火和苛政中聊以自慰。
支道林作为魏晋般若学的代表,以"即色本空"的思想宣扬般若性空理论,但从现有文本来看,他并没有从佛教角度对"有待的自由"问题给予解答,但从他的佛教思想来看,他更注重无待的自由------性空------如何实现的问题,即注重对般若性空义理和方法论的阐发,以及如何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济世渡人。郭象试图用"性分""有待的逍遥"为战乱丛生的现实社会以及儒家纲常名教赋予合理性,并为本体的自由和无待的"玄冥之境"提供了理论的证明,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自由、普通百姓如何从苦难的现实世界超脱出来,相较于当时的佛教思想,郭象的论证是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