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P-ISSN 3022-0335
- E-ISSN 3058-2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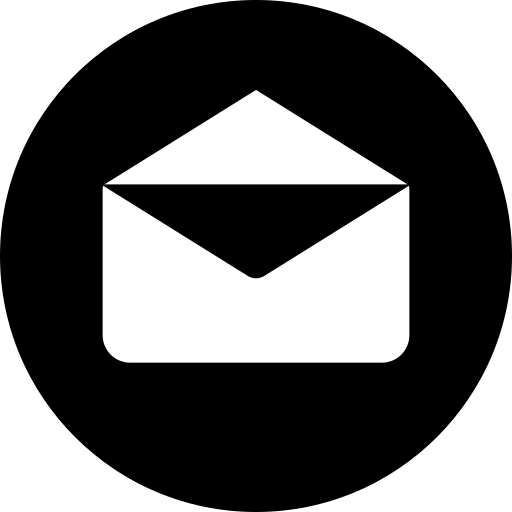
马仙信仰是信仰神祇马氏天仙(又称马元君、马仙娘、马仙奶等)的民间信仰,唐宋间肇始于浙江南部括苍山区缙云县(今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村,逐步流传于闽浙及毗邻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马仙信仰拥有了以"孝"为核心的多重神灵形象和丰富的神灵传说,在信仰传播地浙南、闽东、闽西、闽南等地形成并保留了神灵塑像、灵岩洞府、宮观庙宇、祭祀组织、仪式活动等多种內容的文化景观。"景观"视角的引入将丰富马仙研究的"文本",即从传统的方志、碑记、族谱等文献史料拓宽为文献与景观并重的文本。通过对文化景观开展分析,得出马仙信仰文化景观承载的观念表达,深入理解景观所处的地方文化,为地方文化景观在现代的再生产提供思路。
The Ma Xian faith is a folk belief in the deified figure known as Ma Tianxian (also referred to as Ma Yuanjun, Ma Xianniang, Ma Xiannai, etc.), which originated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southern Zhejiang region of the Kuocang Mountains in Yun County (modern day Jingning She Autonomous County), specifically in the village of Luci. It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neighboring areas of Fujian and Zhejiang. Over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the belief in Ma Xian has developed multiple divine images centered around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and a wealth of divine legends.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 faith has spread, such as southern Zhejiang, eastern Fujian, we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Fujian, it has formed and preserved cultural landscapes that include the sculpting of deities, sacred grottoes, temples and shrines, ritual organizations, and ceremonial activ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ndscape" perspective enriches the "text" of Ma Xian research, expanding it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such as local records, inscriptions, and genealogies to a text that emphasizes both literature and landscape.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conceptual expressions carried by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Ma Xian faith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culture within which the landscape is situated, providing ideas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he modern era.
厦门大学宗教学硕士,现为青岛黄海学院国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道教和民间信俗文化。主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今礼仪概要"等课程。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仙信俗传承中心"道学传承与成果转化"特别委托课题研究工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文化景观的概念首先被运用于人文地理学,"用于认知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过程与结果"(Huang and Li 2017, 123-124)文化景观作为一种认知视角,"观看方式"对于文化景观十分重要,或者可以说文化景观就是一种"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要被安置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中(Cresswell 2009, 9)。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人类,其观看方式不同,产生的行动也不同,形成的文化景观就不同。
景观是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作为一个有序的事物集合、一个文本,景观承担了某种意指系统的功能,社会系统通过意指系统去交流、再生产、体验和探索"(Duncan 1990, 17)。文化景观作为有组织的文本,具有表达观念的功能,可以被解读出制造了景观的文化实践,而文化景观存在的必要性就体现在其所承载的交流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上。"景观是社会和主体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是主张文化权威的一个场所"(Matless 2009, 231)在这个层面,文化景观被构造的过程就是主体身份形成的过程,文化景观承载的观念表达就是文化权威的主张。
文化景观的概念内涵了空间尺度和时间维度。在空间尺度上,文化景观是文化实践造就的空间体系,内涵了空间与行动的关系,承载的是主体在文化观念指导下在空间中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对自然环境实施改造,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在时间维度上,文化景观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承载了集体记忆和地方历史。
基于以上对文化景观的理解,文化景观视域下的马仙信仰,首先要关注到马仙信仰中的空间尺度,这种空间尺度体现在马仙信仰所处的区域地理环境、宮观庙宇建筑、迎仙科仪以及游神路径,解读这类文化景观表达的观念;其次要关注马仙信仰的时间维度,在地方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脉络中找寻理解马仙信仰的关键要素,分析其文化景观所主张的道德价值。
马仙信仰是信仰神祇马氏天仙(又称马元君、马仙娘、马仙奶等)的民间信仰,唐宋间肇始于浙江南部括苍山区缙云县(今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村,逐步流传于闽浙及毗邻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马仙信仰拥有了以"孝"为核心的多重神灵形象和丰富的神灵传说,在信仰传播地浙南、闽东、闽西、闽南等地形成并保留了神灵塑像、灵岩洞府、宮观庙宇、祭祀组织、仪式活动等多种內容的文化景观。本文以福建省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的马仙信仰为研究案例。漈下村的开发历史,至迟不会晚于明朝初年[1]。 漈下《甘氏族谱》大明成化十六年序云:"至七十八世祖伯祥公之孙讳得英公与胞弟得进、得名、得满,携妻一十餘口,於皇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由浙处景宁县张村迁居福建福州府古田县二十二都龙漈境。由是天赐鸿禧,本支百世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屏南历史上长期属福州府古田县管辖。漈下村在屏南建县之前,归属古田县,旧称古田县横溪里二十二都龙漈下村;立县之后,于乾隆元年(1736)改称屏南县横溪里十都龙漈村,简称龙漈洋,俗称漈下。漈下村在明正统年间普遍接受了马仙信仰,经过地方百姓五百余年的信仰实践,积淀了丰富的马仙信仰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性的神灵塑像、宮观庙宇,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传说故事、祭祀组织、仪式活动等。
漈下《甘氏族谱》的一段记载反映了迁居于此的甘氏族人对村庄所处地理环境的解读:
龙漈下即今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甘氏八十世祖甘得英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携亲族迁居于此,甘氏八十一世祖甘细旷是为屏南漈下甘氏开基祖。拓基首要之事,便是堪舆。甘氏族人对村庄所处地理环境开展了堪舆活动,认为此地是"飞凰落洋之象",指凤凰落在相对开阔的平原上。经实地考察,漈下村正位于山间盆地,然而何来"飞凰?"要看到"飞凰",离不开对"风水"观念的前理解,在风水堪舆学上对于地理形制有"喝形取象"一说,就是直观此地形制宛如飞凰。拓基之时的风水堪舆是景观形成的重要文化实践。
龙漈仙宫坐落在双溪汇合的角洲之上,坐南向北,与双溪出处"层峦屏"遥相呼应,构成龙凤相配的风水格局,而且凤落龙上,有镇水之意。龙漈仙宫又名登瀛宫、仙奶殿,仙宫主祀神是被村民称呼为马仙奶的女神马氏天仙,配祀神分别是叶大都元帅、卢相公、马相公以及两位本地拳师甘曹、甘六(下文详述)。仙宫主殿悬有"方壶圆峤"匾额,呼应其"天圆地方"的建筑构造样式,建筑立面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十分罕见。龙漈仙宫采用这一罕见的建筑样式,当与马仙"浮伞渡人"的传说有关,伞的意象也指向了马仙"罗伞济世"的功德。龙漈仙宫内部的建筑构造也与风水观念呼应。如图所示,龙漈仙宫月梁上的凤凰高于金枋上的龙,构成"上凤下龙"的形象,可以看作是"飞凰落洋"堪舆实践的结果。漈下甘氏将马仙视为开疆拓境保护神,这一信念指导了他们的实践,即对于马仙是开疆拓境保护神的信念指导了主体要在龙漈仙宫塑造"上凤下龙"形象,以此呼应"飞凰落洋"的地理形制。
龙漈仙宫是人为构造的空间体系,但它内部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与自然的关联。"(景观)将文化和社会建构自然化,表达一个人为世界,好像它是某种给定和不可避免的"(Matless 2009, 1-2)。仙宫梁上有一副墨书"文峰长对峙,剑水永洄澜",金柱上写着"保赤民呼母,成丹品列仙",人们对龙漈仙宫的期望是与文笔峰和漈水一样长久永远,对马仙的认知是她如母亲般护民如子,因此而位列仙班。每一个细节都在为"自然化"努力,让龙漈仙宫成为某种给定和不可避免的"信念景观"(Anderson et al. 2009, 403),这种自然化恰恰赋予了龙漈仙宫以神圣性。经过这样一系列建构,一个人间仙境呈现出来。龙漈仙宫的庙门上用了这样一副对联,"蓬莱弱水惟飞仙可渡,方壶圆峤乃仙子所居",作为被构造的文化景观,表达出漈下人对栖居之地的观念。
在漈下村,龙漈仙宫与迎仙桥、云路门共同构成了马仙信仰的空间序列。这一空间序列的构成可以从甘氏家族的信仰实践中考察。漈下明朝时的古村沿双溪的东溪"坐东向西"分布。"云路门"(俗称城门楼)是古村的北城门,城门楼高二层,坐南面北,与文笔峰相望。门内即漈下古村,沿溪分布形成三横两纵的"臼"型布局;门外正通迎仙桥(又称"花桥"),"乡之花桥,坐南向北,桥头有水碓店肆,往仙宫经此"(《甘氏族谱》)。花桥的位置是古村居民去往龙漈仙宫的必经之路。花桥为廊屋桥,廊内设有便于村民闲坐休息的长凳,加之所处要道,极容易聚集群众,历来是"公议堂"。
每年农历六月,漈下村要迎马仙。迎仙的日子是由甘家长辈到龙漈仙宫"问女神"。通常五月初四日清晨到龙漈仙宫请马仙择定出宫巡境的日期,从六月初一开始问女神,用掷杯的方式,掷出"二杯一阳"(连续两次一阴一阳,第三次是两个阳),表示马仙同意了这个日子。今年马仙择定的日子是六月十四。农历六月十四日这天,迎神赛会如期举行,持续三天两晚。在龙漈仙宫主持醮仪的法师历来出自漈下甘氏家族,今年主持醮仪的是漈下甘氏代字辈的甘代赐法师。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笔者记录了2024年7月19日到21日三天的科仪:
(Table 1. Arrangement of the Welcoming Deities Parade Ritual)
| 时间 | 科仪 | 地点 | |
|---|---|---|---|
| 六月十四日 | 早上 | 发奏、请神、造楼、供器等 | 龙漈仙宫 |
| 下午 | 起马供(马仙出宫巡境)下马供(马仙回宫) | ||
| 晚上 | 晚供,请神去戏院看戏;半夜供(戏院演出结束后),请神回宫。 | ||
| 六月十五日 | 早上 | 做早供、起马供、拦马供、下马供 | 龙漈仙宫/城门楼 |
| 中午 | 做午供 | 龙漈仙宫 | |
| 下午 | 请神去戏院看戏,(演出结束后)请神回宫 | ||
| 晚上 | 做晚供,请神去戏院看戏;半夜供(戏院演出结束后),请神回宫。 | ||
| 六月十六日 | 早上 | 做早供,起马供,拦马供、下马供 | 龙漈仙宫/城门楼 |
| 中午 | 做午供,献供谢神 | 龙漈仙宫 | |
| 下午 | 送神 | 龙漈仙宫 |
第一天游神队伍的"排头"是甘丽湖,甘丽湖夫妇在漈下村经营一家民宿,民宿的位置就在龙漈仙宫对面。对于游神路线的规划,他说,"我走哪条路,后面的人就跟着走哪条路,但是无论怎么走都要过城门。"过城门指游神队伍从云路门经过,其含义是"出城"和"回城"。排头负责扛起的神牌上写着,"敬神如神在",之后依次是"恩沛龙漈"神牌、明制香炉、马仙香火牌位、叶大元帅轿辇、马氏天仙轿辇以及八仙(由戏班演员扮演),队伍中穿插着锣鼓、大鼓、花鼓队、各式仿制兵器、华盖、令旗,队伍最后是拿着各色彩旗的大人孩子,多数是归乡游子。笔者跟随游神队伍记录了2024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每日的游神路线(图1-3),这三天的路线即有重合的部分,又有不同的地方。重合的部分是由龙漈仙宫出发,经迎仙桥------峙国寺------官厅厝,抵达城门楼,从云路门东门进北门出即"出城";而游神队伍回来的时候要从城门楼北门进再从东门出即"回城",经官厅厝------峙国寺------迎仙桥,回到龙漈仙宫。游神路线不同的地方是在漈下村四至范围内绕大圈还是小圈的区别。游神路线的选择,考虑了尽可能多的经过更多的村民门前、村庄田产和重要的公共空间。手持香火站在路边虔诚敬拜的村民、被途径的田产和公共空间,都接受着马仙奶的照看,也因此确认了自己的身份,既是马仙的子民,又是甘氏的后人。
"理解(并因此改造)景观的关键包含了首先要理解如何------以及特别是在哪里、由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景观被制造出来"(Matless 2009, 233)通过集体记忆与地方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活在景观中并创造了景观的文化,可以进一步解读文化景观,形成对马仙信仰的再理解。
屏南漈下甘氏八十二世祖甘思玉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玉幼时熟记叔父遗言,吾宗籍棣浙江处州景宁县四都六源张村。始自万十二公讳永耀,至吾祖得英公兄弟四人为充里役,解纳坑课钱粮,中途失盗,倾家赔偿。乃于大明正统二年(1437年)率子侄二十余口弃祖基于张村,择迁居古田县龙漈。"在《甘氏族谱》记载的这段文字说明了漈下甘氏由浙江景宁迁徙至福建古田龙漈(今属屏南)最直接的原因,即"解纳坑课钱粮,中途失盗",发生这一事件的历史时期不晚于明正统二年,应是宣宗时期至英宗即位之初。所谓"坑课"即指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等矿场依矿利数额向官府缴纳的税银。明时处州银矿缴纳税银在整个浙江省占有一席之地,"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明宣宗时期,浙江矿场的岁课增加到九万馀两。矿盗现象伴随着矿场开采而来,蔡逢時撰《温处海防图略》谈及处州防矿四至,"处州十邑皆僻,处万山,矿坑甚多。先年奉例开采,未开采者惟丽水、靑田、缙耳。盖田少民穷,垂涎利源,相习盗矿,如国朝巨寇陈见湖等咸起于此,远近骚然。"民生多艰,矿利诱人,百姓为糊口谋生成为矿徒,流徙于万山僻壤之间,私开矿坑或盗取官矿银课,《甘氏族谱》所记载的甘得英兄弟四人解送矿场税银之时遭遇盗贼侵夺的情景,正是明朝中期浙闽山区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景观。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施行里甲制度,至明正统间浙江开始实施均徭制度,甘得英兄弟四人"充里役,解纳坑课钱粮",是明代赋役制度下民收民解运纳体系的体现。坑冶获利要向中央政府交纳钱粮,每年钱粮交纳就需要派役民差解,收户、解户、马户是里甲常设之役,服务于运纳钱粮。《衢州府志》的记载详细记述了百姓差解之苦:
差解之难也甚矣。大户之苦也,领出库银则有倾销之费,解粮就道则有水脚之费,投纳公门则有常例之费,临时交兑则有添搭之费。差解之水脚本有帮贴也,苟非廉吏谁肯给之帮贴,归于无何之乡,而水脚出于大户之自办矣。钱粮之倾锭本系全数也,一两之除谁敢诘之。元宝倾于大户之手,而千两内有二十两之增添矣。批迴之赴销,本难刻期也,违限一日即罚谷数十石......或其官贤明不肯扣除,则用胠篋探囊之巧计,当解银未全之际,请官允给。官令解户当堂允过其数,原足硃笔摽封,官谓无恙矣,仍令贮库候允足全给。然后库吏从容将前硃封拆開就内除去一两,仍照原封不动,及发与解户,吏云'官照例除去'。解户不敢问也,剜肉赔偿叫阍无计。[2]
解纳钱粮之苦,苦在官吏衙役的层层盘剥,所运钱粮处处遭算计,几无保全之可能。一旦钱粮失盗无法交差,面临的即是"倾家赔偿"。甘氏家族遭遇解纳坑课钱粮失盗之灾,不得不弃祖基迁徙避祸,从浙江景宁出发,最终在福建屏南找到安居之地。屏南首任知县沈钟在《屏南县志》兵防一章中写道:"屏邑向为逋逃薮,邻里境人咸呼为里头,不敢深入......","逋逃薮"即藏纳逃亡者的地方,屏南重峦叠嶂,森林茂密,历来就是隐匿避祸之地,相应而来的是生存条件的艰难。在这种历史境况下,甘氏家族开始了对漈下自然环境的改造。
文化景观是一段人类改变的自然,但是被改变的自然服务于一个独特目的:形成文化的需要和渴望。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中,漈下甘氏选择了马仙信仰,形成了习武之风。马仙信仰能够满足漈下甘氏对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是由于马仙信仰发源地景宁是漈下甘氏的祖籍地。通过传承与发扬马仙信仰,甘氏家族得以在异地他乡维系与祖籍地的精神联系,强化宗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马仙信仰中的保境安民、护佑一方等理念,与甘氏家族在迁徙过程中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安全隐患相契合,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最重要的是马仙信仰的道德价值以"孝"与"忠"为核心,既能够维系血缘宗族的纽带,又能够为习武之风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在漈下甘氏的社会生活中,习武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更是一种传承家族文化、展现家族精神风貌的重要途径,而马仙信仰所倡导的"孝"与"忠",则成为习武之人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他们通过习武来锤炼意志、锻炼体魄,同时也将马仙信仰中的道德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和精神风貌。漈下甘氏武将辈出,第九代甘国宝(1709---1776年)是甘氏家族文化孕育的武将代表,他是清代著名将领,曾两度担任戍台总兵,为保卫和建设台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出过重要贡献。
"景观是社会和主体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是主张文化权威的一个场所"(Matless 2009, 231)在这个层面,文化景观被构造的过程就是主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在龙漈仙宫,马氏天仙的塑像位居神龛正中,显示了马仙是龙漈仙宫的主神,在其神龛两侧是这样一副对联"开疆境功高德重,保赤民母爱娘慈",上面悬有横匾"功高漈水"。这副对联宣示了这一空间的权威主张------马仙是开疆拓境的保护神,是慈爱的母亲,护佑着漈下子民。在漈下村走访之时,时常听到马仙是甘氏家神的表述,以及认为马仙就是甘氏的老祖母,所以甘氏后人都称呼其为马仙奶。主持马仙信仰仪式的法师------甘代赐,是漈下甘氏"代字辈"人,显应灵坛闾山派法师,在龙漈仙宫的信仰空间中,他被尊称为"先生",是信仰空间的文化权威。甘法师提到,"科仪本上写着,马仙是处州府景宁县横山岭南朝大殿敕封护国马氏天仙,我们的马仙是从景宁来的"。同样从景宁而来的,还有漈下甘氏,"皇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由浙处景宁县张村迁居福建福州府古田县二十二都龙漈境"(《甘氏族谱》),景宁是漈下甘氏的祖地。在龙漈仙宫被奉祀的马仙,表达着所有漈下甘氏族人对祖地的确认、对身份的认同。
马仙左右两侧的配祀神,除了叶大元帅、卢相公和马相公之外,还有甘曹、甘六两位拳师。田野调研过程中,笔者随机询问前来上香的信众,是否知道马氏天仙右侧三尊塑像分别是哪三位神灵,得到的答案大部分是"不清楚",少部分信众介绍说"是我们本地的拳师"。在仙宫中做斋醮科仪的法师甘代赐给出了三尊塑像身份的解读,分别是马相公、甘曹和甘六,当笔者进一步追问这一答案来源时,他回答:"我们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这里,祖先的文化权威性彰显出来。甘曹、甘六何时进入了马仙信仰的神灵体系?笔者在《漈下村史------续修甘氏家谱(1914-1991)》找到了关于甘曹、甘六的详细记载:
继国宝公、攀龙公习武中举(约在清乾、嘉时期)之后,村人不图功名唯求自卫健身,认为学武器不如学拳便捷。当时,少年甘曹、甘六兄弟,遂前往闽南一带寻访拳术名师,在永春巧遇少林虎拳真传名师郑礼泰之子郑元辉师父,当即礼聘莅漈传授。由于曹、六兄弟为人忠直正派,礼待师父一片至诚,敬如上宾,学拳中又能谨遵教导,狠下苦功,从而感动师父,以为传拳得人,经六年苦练(一般只三年),全套少林虎拳与治伤验方,得到元辉师父真传。曹、六虎拳功成后,毫不骄傲自满,仍勤习苦练精益求精。未几兄弟二人受聘同往宁德城关设馆传拳。相传一次曾因路遇不平,于碧山街教训地霸、恶棍而大显身手,打得众多歹徒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当地群众拍手称快,兄弟威名大震宁德城,传为佳话。
曹、六兄弟自宁德完馆归里后,认为家乡历代学武功底厚、武德佳,应将自己所学虎拳在村里广为传授,使人人能拳,既能健身又可保村自卫。遂即在家设馆不计重酬,首先邀集友好青年参加学拳,培养骨干,继则鼓励首批良徒以徒带徒办法,订立馆规,在村里遍设拳馆,大批招收青少年学习,把教习虎拳引向高潮;其次,为便拳不离手,习之以恒,还规定每年秋后农暇,均应复馆练拳。因此当时村里练拳空气浓厚,拳师不断涌现,而外出传拳、治伤者也大有其人。从而我村武术声名大振,武德盛扬,还被各地誉为'拳头秀'('秀'系方言,指巢、窝,这里比喻人人能拳之"武术村")。自此,我村练拳习武,干劲愈大,新秀辈出。
从村史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甘曹、甘六对于漈下甘氏将习武传统发扬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功绩也从未被甘氏后人遗忘。通过村史的记录和塑像,后人追思先人功绩,奉祀不辍。甘曹、甘六融入马仙信仰文化景观的过程,体现了漈下甘氏对地方文化的塑造,在地方历史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前漈下马仙信仰迎仙的组织形式是"生产队",这不同于大部分马仙信仰传播地以"境"为组织的形式,也不同于漈下历史上迎仙的组织形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通过田野调研和查阅地方档案史料,对"生产队"作为漈下马仙信仰迎仙组织形式做出一定的解读。
在漈下,每年的迎仙活动以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生产队为组织,上七队和下七队轮流负责组织活动。所谓上七队即一、二、三、四、五、六、七队,而下七队是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队,也就意味着漈下一共有十七个生产队。查阅地方档案史料发现,际下大队(际下即漈下,为人民公社时期的特殊写法)在人民公社时期总共只有十三个生产队。起草于1958年4月30日的《关于际下乡"三社合一"试点工作的总结报告》记载:
<disp-quote>际下为本县一个较大的行政乡,交通称便,中贯古屏公路外,还有纵横交错的乡间大道,货运顺畅,为历史商业基地。乡辖自然村十个(即际下、小梨洋、巴地、板兜、东洋、梨坪、芹山、洋头、左坪、洋头仔,其中50户以上有四个,50户以下有六个),572个农户,2153个人口,除耕地10056.56亩......全乡建立起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十个,参加组织的农户达556户,2109人,占总户数97.4%。</disp-quote>
《关于支援穷队情况的报告》起草于1966年12月8日,漈下已经成为甘棠公社漈下大队。文中提到漈下大队位于文笔峰南部,有三个自然村,三个山厂,全大队现有245户,1048人(其中男587人,女461人),全劳力215人,耕地总面积3735亩。屏南县人委文件屏民社字第536号《关于发放贷款支持际下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通知》回应了中共漈下大队支部漈下大队管委会请求支援的报告,文中指出,"根据本委驻你社际下大队工作组调查摸底,该大队现有245户1048人包括三个自然村、三个山厂,耕地面总面积3735亩......"
出自屏南县甘棠人民公社漈下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1973年度农业年报"记载了甘棠公社漈下大队组织情况,其中"生产队数"一栏写有生产队13个,社队名称一栏记录了13个生产队名称,以队长名字为记,如1队甘代康。每队的入社户数、入社人口、男女整半劳动力情况均有清晰记录。
结合以上资料分析,漈下村迎仙活动以"生产队"为组织,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土地公有制彻底改变了原宗法制下祭祀组织的经济基础。根据笔者走访了解,龙漈仙宫原来是有庙产的,庙产的收益用作迎仙活动,而管理庙产的人是家族内部各房各支轮流。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当事人多数健在,是活的历史。在漈下村走访询问村民是否知道自己是第几生产队,全部脱口而出。三是人民公社时期中断了迎仙活动,旧组织形式被新组织形式替代。随着人民公社时期的结束,生产队已经失去了实际功用,而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在马仙信仰文化景观中,这个符号有着清晰的意指,它指向强有力的组织,能够保障迎仙活动的有序进行。
马仙信仰文化景观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在空间之维,通过考察漈下村风水空间与信仰实践的互动,我们看到文化景观是如何被构造出来,以及其所表达的文化观念。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将马仙信仰文化景观放置到历史与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看到漈下甘氏选择马仙信仰的原因,理解马仙信仰的道德价值在家族习武之风与地方文化塑造中的作用,也解读了当下漈下迎仙活动以"生产队"为组织形式的原因。马仙信仰文化景观的形成中,人的主体性发挥着积极作用,被构造的景观本身承载了人的观念表达,体现为多个方面的价值追求,其中较为凸出的是忠孝、慈爱与安康。
首先,从忠孝的角度看,马仙信仰所倡导的"孝"与"忠"不仅是家族内部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石。甘氏族人通过习武、修建龙漈仙宫、组织迎神赛会等活动,不断强化这种道德观念;甘氏家族武臣辈出,以甘国宝为代表,"发扬武功,力行善事"成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慈爱在马仙信仰文化景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村民对马仙称以"马仙奶",还是龙漈仙宫"母爱娘慈"的楹联,乃至"过半年"游神时分发粽子的集体记忆,都展现了对慈爱美德的追求,成为连接不同家族、不同群体的情感纽带。最后,安康是甘氏族人追求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他们通过改造自然环境、精心规划村庄格局、奉祀马氏天仙等方式,努力营造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马仙信仰以"旱祷辄应"著称,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被赋予了保佑地方平安、风调雨顺的神圣职责。马氏天仙的存在,不仅为甘氏族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也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应对生存挑战的信心和勇气。
综上所述,马仙信仰文化景观是地方历史、社会结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复合体,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在涉及闽浙多地的空间范围和近千年的时间维度上,马仙信仰文化景观得以普遍的保留下来,在现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这种"持久性"值得进一步探究。